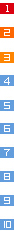《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劳佳迪 | 上海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26期)
这几天,“野人”杨欣从姜古迪如冰川(编者注:位于唐古拉山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长江正源沱沱河发源于此)踏雪归来,胡子已经可以用作羊毛围巾了。从2005年开始,以身体丈量长江源的生态面貌,几乎成了这位民间环保界传奇人物的日常。
杨欣是中国第一个民间自然保护站的建立者,当年在他建议抢救藏羚羊之前,这些高原精灵一度被猎杀得只剩下10头。他现在掌舵的四川省绿色江河环保促进会(下称“绿色江河”)是经四川省环保局批准,在四川省民政厅正式注册的中国民间环保社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曾多次对话杨欣,不论是在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里腹地,抑或是紧紧挨着青藏公路的唐古拉山镇,还是成都的办公室里,他都直言资金缺口带来的公益困境。
对于没有公募权又不接受冠名赞助的绿色江河来说,除去从地方基金会获得募款,过去公益支出有一部分还要依靠杨欣一本一本义卖自己的著作。不过,去年发起网络众筹项目在一个月内筹得14万元,让他意识到“互联网公益”可能释放出新的公益量能。
据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翟红新对《中国经济周刊》披露,去年网络公益筹资额达到了5.4亿元,超过2014年之前5年总和的5倍之多。
另一方面,当善款纷至沓来,其真实用途的透明程度也考验着“互联网 ”模式下整个公益生态圈的净化功能。
互联网让草根NGO能分享公募权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国内最稀缺的公益资源其实并不是善款本身,而是公募资质。根据现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非公募基金会不能面向不特定公众筹款,意味着公募权长期被官办基金会和慈善会垄断,如何获得长效的资金支持一直是NGO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腾讯公益平台上,草根NGO组织也不可以直接上线项目,要先发布到后台,由公募基金会甄选出优质项目来合作,再由我们审核发布,最终募集的善款必须先进入公募的对应账户,但互联网已经为分享公募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翟红新在6月16日召开的首届互联网公益峰会上对记者解释。
事实上,真正优质的公益项目并不缺少认领者。专注于关爱抗战老兵领域的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去年募资总额达到了4950万元,在腾讯平台上线后,网络善款超过了1000万元,延续了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长期合作。
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创办人张淑琴去年在几周内就通过平台项目认领筹得400多万元善款。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薛一心透露,去年11月才上线的项目在5天内就筹到了168万元,“这改变了我们全年的筹资策略,今年希望25%的善款来自互联网。”
杨欣也对记者表示,绿色江河在腾讯平台上的项目虽未上线,但目前已和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达成了意向,进入到项目文案修改的环节。

数据来源:民政部所属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 编辑制表:《中国经济周刊》采制中心
本身规模体量占绝对优势的公募基金会更是这场互联网公益盛宴的受益者。壹基金不仅在2009年前后曾与马云会谈,更直接参与了腾讯互联网公益平台的研发。“2011年,壹基金的公众捐赠占到全部捐赠金额的50%左右,2014年壹基金公众捐赠首次达到全部筹款额的72%,2015年公众捐赠占比也超过7成。近两年来,每年都有上亿人次通过互联网向壹基金捐款。”壹基金秘书长李劲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秘书长王林也对记者分享了一组数据:2015年儿慈会总筹款近2亿元,80%是个人筹款,其中有62%来自互联网,3年前这个数据仅为8%。
“去年善款总额达到了3800万元,而互联网善款就达到了1293万元,这相当于往年募捐总金额数。”2013年才拿到公募执照的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刘正琛完整经历了互联网公益的发展过程,“5年前我们就做淘宝店,2012年尝试新浪微公益,那时网络公益比较小众,每年募捐额也就一两百万元,2014年接触腾讯平台,这一年只筹到14万元。”
因为当时筹款结构还依赖于几家大企业,一家煤炭龙头少捐了两三千万元,直接造成基金会2014年善款下降25%,这种窘境在互联网公益时代被真正打破。
公募不满足做“钱盒子”
不过,多位受访人士也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公募暂时变身民间NGO组织的“钱盒子”,并不是互联网公益的终极模式,而是公募权没有完全放开背景下的一种过渡。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周庆治形象地对记者描绘了正被突围的公益格局:“中国公益一开始就是第一部门(政府)覆盖,第二部门(企业)发育,第三部门(民间)才有七八年历史,公权力是‘象腿’,企业是‘牛腿’,NGO只是‘鸡腿’,还无法三足鼎立,如今的‘互联网 ’模式是将公益从很小众的圈层带了出来,第三部门的孵化和成长将得到空间。”
因为在互联网领域起步较早,李劲已经在思考未来公募怎样真正加深与民间NGO的合作,而不仅仅是作为过账的“钱盒子”,“在腾讯平台上,我们还没有认领过项目,都是以自己设计的产品为圆心,分给不同的NGO伙伴去执行,未来公募、非公募界限肯定会完全碎裂,所以年初我们就开始思考联合公益的形式。”
据李劲对记者解释,联合公益将围绕一些大议题鼓励当地NGO解决当地的社会问题,壹基金担当的是出资支持地方枢纽机构的职责,由此形成一个全国网络,“目前我们正在计划采用联合公益的形式,与其他公益组织合力探索解决乡村儿童发展的方法。”他还透露,区域性的协调组织一般是在专业领域富有经验和影响力的公益组织,规模较大、具备较完善的组织架构。
在刘正琛眼中,除了上述这种资助型机构和执行型机构合作的形式外,公募与草根组织的结合还可以有许多维度。“包括不同行业的合作,例如抗战老兵和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以合作,白血病救助和公益顺风车之间可以合作;还有同行业的合作,比如爱心衣橱和免费午餐之间可以共享乡村儿童的信息,白血病救助的公益组织可以共享患者的信息等。”
在他看来,美国的职业筹资人协会就有可借鉴之处。“每个公益组织都有筹款部门、项目部门、人力资源部门、传播部门等,如果自己组织培训会花费很高成本,不同公益组织在细分领域中能有专业合作就更好,比如美国的这个协会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筹资的方法。”
互联网是否让善款去向更难追踪?
谁也无法否认,去年井喷后的互联网公益很大程度让原本颇受掣肘的资金支持得以松绑。早在2014年国内善款总额就已超1000亿元人民币,虽然远远落后于美国3000亿美元的数字,但美国仅有14%大众捐款来自移动端,中国个人捐助中的移动端用户高达84%~85%,已经凸显出中国式互联网公益的结构特征。
曾轰动一时的“郭美美事件”虽时隔数年,仍令公众心有余悸,如今隔着屏幕,更引发不少捐助者叩问:如何确保每个项目的真实性?善款去向是否更加难以追踪?是否会有账目不清的机构鱼目混珠?
对此,翟红新认为,可以信任互联网的自我净化功能,“这使公益项目形成了7×24小时全天候被观看的环境,是可以产生优胜劣汰的,互联网让信息传递的成本变得很低,公益信息传递者和受助者的界限也更加模糊,一些救助案例的参与者就能让信息生产变得更透明,比如一场医疗救助中,手术医生就担当着信息真实性的背书,而朋友间传递信息其实更容易信任,腾讯平台还提供了一个‘我要反馈’的服务接口,实名和真情实感的反馈也是有助于项目透明的。”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互联网提供了与捐助者直接对话的可能性,这本身也是有助于透明度建设和信任培育的,“今年5月,基金会为了帮扶雅安果农发展,通过移动互联网为他们预售1000多份车厘子,却因为一场意料外的大冰雹造成绝收,本来我们担心一旦公布实情,公众会不接受,煞费苦心经营的微信公众号粉丝会急速减少,但是我们公布了果农受灾的消息及退款账号,及时真诚与用户沟通,没想到不少用户纷纷表示不用退款,选择将钱转捐给受灾农民,公布当晚粉丝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300个。”
“透明是赢得信任的手段和途径,而不是目标,公益组织追求的最终目标是项目执行的成效,透明是底线,只是因为现阶段透明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所以公众比较关注,未来希望透明不再是一个问题,公众不再谈论透明,只谈效用。”刘文奎如是说。
李劲还指出,互联网公益现有的信息披露模式主要是公益组织通过互联网平台向捐赠人汇报,他认为这其中还存在可以优化的空间,“目前公益组织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得的捐赠人信息并不完整,只能通过互联网平台向捐赠人反馈信息,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捐赠人管理系统,通过与捐赠人的直接汇报和互动,更好地问责并维护捐赠人,实现服务的及时性。” | 


4a79cbc8-5683-4ead-9dc8-b7fa345312e4.jpg)

21ce1358-5a69-4245-96b9-f1ba9a1f3c4b.jpg)

a2e51174-8d14-4088-ba1a-54cc2cfba46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