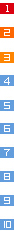热火朝天的筑路工地。

哪怕是铁山也要劈两半。
“我们是‘背’着公路走进西藏的!”
这是我的父亲在讲述修筑川藏线的经历时说的一句话,虽然当时年少的我还不甚解其中的含义,可也感受到了它的不寻常,深深地记在了心里。他说这句话时的语气很平静,但却让人能够感受到他的自豪,和其中不同寻常的酸甜苦辣,感叹只有亲历者才会说出如此深刻的话语。
用激情和希望打通公路
我的父亲翟寿亭,当年是18军54师162团的政委,后调到昌都后方后勤部。1955年调入防空1师,1958年从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后,派往高炮1师,1964年调任空军总医院政委,1979年逝世,国家民政部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虽然修路进藏只是他人生中短短的几年,但是这几年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
父亲告诉我:他一生中有两个最苦的时期,其中之一就是修路进藏。在高原的险峰峻岭上修路,真的是太苦了,可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激情和希望,期望着胜利的一天。
川藏线上的最高峰雀儿山,藏语叫“绒麦俄扎”,意为“雄鹰飞不过的山峰”。公路是1951年10月开工,这座海拔6168米、没有人烟的大山已是天寒地冻,白雪皑皑,公路最高要修到海拔5050米。天气一天几变,晚上气温能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哈气都结冰,水烧不开、饭煮不熟,太阳出来白雪反光让人睁不开眼,有人得了“雪盲”。面对着封冻的雪山,他们喊出了“铁山也要劈两半,不通也得通”的誓言。积雪下的冻土坚硬无比,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砍来树枝烧火、烤化后再打炮眼,使工程进度提高了一倍多。部队涌现出千锤英雄杨朝贵,虎口震裂了,用粗线缝起来,仍旧奋战在工地;有坚强战士杨海银,脚肿得像要爆裂了,用破布裹着继续劳作;爆破能手秦景跃,掏空了棉衣作炮捻,用不断的炮声劈开一切阻挡……
说到在雪山上的“钢丝床”,那是在雪地上摊放一堆形状不一的树枝、上面铺着薄薄褥子的床。躺下的时候身上被硌得根本睡不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褥子又湿了——原来是身体下面的积雪融化了,为战友们的乐天精神所感叹。父亲非常痛心地说道,塌方时战友被埋在了大石块下,因为石块太重,根本没有能力搬开,只好修整一下大石块,就作为他的坟茔。在烈士墓前,大家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打通雀儿山》:
提起雀儿山,自古没人烟;
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
人民解放军,个个是英雄,
雀儿山上扎下营,要把山打通。
……
在父亲的讲述中,充满了对当年生活的感慨,对战友们的思念和对成功的得意,从没有过一丝的抱怨。
重走父辈之路
但是说到真正理解“‘背’着公路走进西藏” 的深刻而丰富的内涵,还是在我重走了川藏路之后。
2001年6月,部分原18军的后代相约重走了这条父辈们修筑的川藏路。当我们一行人沿着当年筑路大军的足迹走进西藏时,我才感到虽然从小就知道“川藏路”,可过去的认识是那么肤浅。
我们是坐着汽车、用了13天的时间走完了父辈们历时4年半修建的川藏公路(北线),这13天与4年半就已经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条2000多公里的公路,沿途的别样风光让人感到新鲜、兴奋,可是一路上十几座海拔4000—5000多米的高山,让我们尝到了人在高原的苦头。6月天山顶还是积雪遍野、风大寒冷,车在山路上盘旋,人已感觉头痛欲裂、口唇乌紫、有人恶心呕吐、呼吸困难,连大声说话后都感到气喘吁吁,就像刚干完体力劳动;腿上就像绑着块石头抬不起来、走不动路;每座山的山顶垭口我们最多也就停留半个多小时。特别是在翻越海拔5050米的雀儿山垭口时,体会到了“爬上雀儿山,鞭子打着天”的意境,很多人也被高原反应折磨得痛苦难当。
可是公路就在我们的脚下,并且绵延不断地一直伸向远方。在这自然环境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60多年前它就的的确确地出现在这里,完全依靠人力肩挑手提、仅凭着锹镐、炸药等简陋的工具和捉襟见肘的生活给养,这是需要具备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和毅力才能够完成的啊!回到车上时我们大家都沉默不语,有些人在流泪,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够表达此时的心情,看着眼前这条飘在天上的漫漫长路,感到即使是用过去认为很了不起的“伟大”这个词,都显得那么单薄无力,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出我们内心的震撼。
父辈们用血肉之躯“背”出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壮举,凭着超凡的精神和毅力背出了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
近些年,川藏公路的历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修建公路对于西藏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意义得到更深入的认识,“‘背’着公路走进西藏”也逐渐被人们所知晓,无不为之感动! 2014年10月在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举办了纪念《为人民服务》发表70周年的“为人民服务讲唱汇”大型演出,在“英模篇”中,修筑川藏路演讲的标题就是“‘背’着公路走进西藏”,引起现场观众热烈的反响。
“‘背’着公路走进西藏”这句来自亲历者的朴素话语,虽然只有简简单单的8个字,却非常准确并且高度概括了筑路部队4年多的浴血历程,它的感召力,让人难以忘怀! | 




2eceaf92-c418-4ffb-9aed-ac32fb2a9cac.jpg)
9a8d2b18-5520-4f3e-8223-87c2c290f204.jpg)
9d174b3f-02c3-4126-bc0e-86858e9ccd03.jpg)
90f90fc7-ca04-4679-b7ba-00d25820bd2c.jpg)
7f5634be-89e6-49bf-a833-0735708f6aae.jpg)